千里江山 万里仁心
李光诗语接民心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光雕像。李幸璜 摄

清末民初手抄本《庄简集》内页。 上海图书馆藏
■ 管仲乐
【编者按】
昨天是今天的历史,今天是明天的历史。回望南宋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,重读被贬琼州的名臣李光之诗,似可重新理解“为政以德”“士以民为念”的儒家理想。
海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管仲乐认为,尽管李光不是朝堂上的柱石之臣,却是民间历史中一盏不灭的孤灯,他用诗书写一座桥,让我们穿越千年,依然听见那句“床头酒一壶,膝上琴一张”,仿佛还在黎家农舍,守着一颗为民不改的初心。
南宋时期,政治动荡,边患频仍,财政困窘,民不聊生。理学兴起之际,一位名叫李光的士人却在诗与仕的交汇处,以一腔忠诚与清醒之笔,描绘出一幅百姓苦乐交织的时代图景。
李光既是理学家,又是实务吏;既是贬臣流人,又是为民请命者。他的诗,不是仕宦的粉饰品,而是为百姓发声的“良心宣言”,字字刻进民间疾苦,句句流露仁政理想。
读书何为 天下为公
李光(1078—1159),字泰发,谥号庄简,出生于北宋末期,南宋建炎初年入仕,时值“靖康之变”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。他的求学背景深受“程朱理学”影响,然其诗文中展现出的却是“理中有情,道中有民”的气质。他在《读书》中写道:“兴亡见俯仰,忠佞更得失。”这是对“春秋笔法”的现代呼应,也是将士子之责从“治国平天下”回归到“识是非,明大义”的儒者情怀。
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多次强调“读书为明理”,李光则更进一步,把“明理”落实为“为苍生谋道”。他在诗中提及“我观宣和间,权幸互当轴。一时名家子,半为阉宦辱。”这对北宋末年的宦官干政、士风败坏有着直观而深刻的批评。与其说他是诗人,不如说他是以诗为刀笔的“史论者”。
李光推崇“以义立言”,而非“以利求仕”。在与后辈学子的交往中,他高度赞扬那些“幽情寄铅椠,雅尚在松竹”的寒门子弟,正如他在《季微季晖昆仲相继见访》中所写,他们虽“雪牖耽夜读”,却以道为志业,显示出士人应有的精神风骨。
诗入田畴 情归乡里
宋代社会经济虽有发展,尤其南方农业生产兴盛,但自然灾害、兵乱频发,百姓生计实难为继。南宋淳熙年间,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岁歉则米石数千钱,百姓鬻子以供租。”李光的诗中,多次呈现出这种“雨旱交迫,民困如斯”的情景。
在《江西久旱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老火擅炎夏,枯旱气欲然。民穷舍耒耜,群起操戈鋋。”旱灾不仅毁田、减产,更导致社会治安失控,百姓不得不转而自保。与史实相映成趣的是,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也记载,南宋中叶江西、湖南一带连年枯旱,民众乏食,群盗四起。
李光对这种苦况的理解,非止于悲悯。他紧接着又写“夜来沧江雨,朝望水接天”,那一夜暴雨让他欣喜若狂,正如《次韵贺子忱喜雨》中所写:“少宽边饷急,聊慰老农心。”这是“及时雨”的快乐,也是“解万民之倒悬”的诗心。他从不把自己当“过客官”,而是与农夫同悲喜、共忧乐。
此外,在《去地草》一诗中,他讲述如何组织百姓清理泉源淤藻,使泉水“滋田免叹嗟”,体现出他对基层水利治理的高度关注。此类内容不仅诗意十足,更与南宋《农书》中反复强调“修渠导水,以利耕作”的理念暗合,反映了他“知稼穑,通民情”的政治实践。
以诗为剑 直陈弊政
在宋代,“士大夫议政”的传统根深蒂固,而李光则将这一传统化入诗中,尤其体现在那首惊世骇俗的《海外谣》里。这首诗以纪实笔法,详细描绘贪官陈建中、王琮等人如何“以女攀权”“图册定价”“逼民起义”,终酿成琼州琼山大乱。
据《宋会要辑稿》卷一百九十三记载,南宋末年海南盗乱频仍,而李光却敢在诗中直呼贪吏其名,指出“致寇之因,实缘赃吏”,这无异于将刀锋指向朝政弊端。他清楚地知道,此诗不会立即改变什么,但他依然写道:“庶几采诗者达之诸司。”愿意将诗当作奏章、当作民意的通道,可谓“士人风骨”的典范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李光并非一味批评。他深知好官之难得,因此在《自然解印北还作古风送行》《喜雨送行》等诗中频频赞扬清官“擒纵出拘挛”“不索钱帛”“里巷绝嗟呼”,希望以诗为旌表,倡廉风于乡邦。
李光褒贬并举、奖惩并书的笔法,使他的诗真正达到了“刺时疾俗”的作用。
一身流离 仁心万里
绍兴十五年(1145年),李光被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与胡铨诗酬唱和,讥讽朝廷,贬谪琼州;绍兴二十年(1150年),他又遭陆升之诬告,以“私修国史”之罪,再贬儋州。他自称“鳏气成,空行蹑飞仙”,可见心境落寞。然而,他并没有消沉。相反,他将这段流放岁月转化为一部诗意的人间纪实。
在《赠裴道人》《载酒堂》《黎人二首》中,他记录下海南黎民的生活:“藷芋饷昼耕,松明照夜勤。”在物资匮乏、文化隔绝的环境中,他没有高高在上地审视“蛮村”,而是深情地记录、理解,甚至与黎族人共酌,与乡老同耕。
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载:海南虽地远天荒,然“征赋繁苛,吏治不明”,不少外放官员借机敛财,苛求民力。李光却主动提出“永宽海外氓,精求二千石”,反复上疏要求减税减徭。他在诗中不止一次描写村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,“独有老农能耐久,路傍犹说长官清”“山畦是处田畴美,时有归牛带夕阳”。这种来自百姓口碑的评价,比起仕途荣辱,更见人格高贵。
李光最终在政局稍稳后被召还北归,《五月十三日北归雷化道中》即为此行所作。他写道:“人生七十稀,况复加九年。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他选择以归隐方式谢世,不以荣辱挂怀,只求“吐纳留真诠,收功在丹田”,回归内心的安宁。这种从民本出发,归于清静的精神世界,也可视为儒释道合流于李光身上的思想结晶。
在李光的诗中,我们既看到“诗以言志”的文人本色,也读出“诗以载道”的士人气节,更感受到“诗以忧民”的民本情怀。他不事繁华,不尚粉饰,始终坚持“为民立言”的信念,在贬所写下了真正属于百姓的诗篇。
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“海南省人民政府”门户网站
是否继续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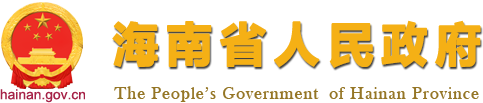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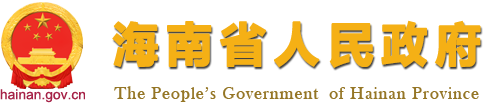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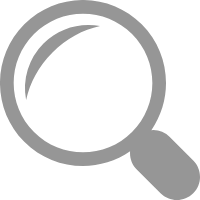

 琼公网安备 46010802000004号
琼公网安备 46010802000004号

